
原标题:痛苦,是咱们自己界说的|《外出偷马》
2007年,挪威作家佩尔·帕特森《外出偷马》取得都柏林IMPAC文学奖,本年因改编电影取得柏林影展银熊奖再获重视,这个月还在我国欧盟电影节播出,惹来豆瓣热话,中译本也刚刚出了新版本。阅览这部小说和欣赏电影,把我带回十多年前一个初夏,我在奥斯陆和挪威的峡湾游逛的时分。
佩尔·帕特森(1952-)今世挪威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实力提名人。曾做过书店店员、书评人、译者和图书馆馆员,直到1987年才开端全职写作。现在已出书九本小说,还有一本散文集。
撰文丨廖伟棠
大天然是北欧六合无情的永久
彼时形象最深的是泠然飘至的雨,时缓时骤,不知所起。然后隔着雨雾,峡湾两旁的森林深处一闪而过会有几间板屋,恬然小隐,就如永久存在相同。
多年后,我在《外出偷马》电影的地景里彻底感触到了这种北欧六合无情的永久,就像导演汉斯·皮特·莫朗说的:“故事里的人物不受外在影响,他们的窘境和抵触与国际无关,由于他们被大天然紧紧包裹着
(乃至是被吞噬)
。这是大天然令人敬畏乃至惧怕的部分,不是由于它很严格,而是过于众多、恒久不变,有时让人难以承受。”
电影《外出偷马》剧照。
不过,电影里简直没有拍出来的,是环绕主角传德半生的,挪威的暴雨,在他外出偷马失利后下起的那一场,在他回到奥斯陆等不到父亲回来时遇到的那一场。
“当然,他没来。来的是等候持久的雨……大雨从艾克伯格的山坡滂沱而下,涌上路右边的铁道,铁轨消失在隧道里再从左面冒出来,一切的房子和修建都比本来的灰更灰,然后消失在雨里,我没了眼睛,没了耳朵,没了声响,终究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所以我停下来不去了。一天不去,两天不去,三天也不去。好像一道帘幕下降下来。简直像是再一次的出世。色彩不同,气味不同,看工作的感觉不同。不仅仅冷与热之间,亮与暗之间,紫与灰之间的不同。而是我对我所惧怕的和高兴的感触都不同了。”
佩尔·帕特森原著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在电影里得到忠诚出现,少量没有,上述这一段便是。但这种逝世与再生感,浸透在电影空镜头里的很多天然元素中,六合无情,却又与人类的悲欢命运似有冥契。电影里充溢夏天意象与冬季意象的转化,但少年传德1948年夏天挪威瑞典鸿沟森林里所阅历的生离死别,奔跑的野兔、幽静的马匹、破坏的鸟巢……都逐个照应了他,并作为夏天之忆,在五十年后千禧年前夕的那个严冬安慰了他。
父亲——赶过实际之上的浪漫主义者
除了1996年的一场事故,咱们不管在小说仍是电影都对1948年夏天到1999年冬季之间在传德身上发作的工作一窍不通。仅有“确认”的是他挺过来了,以他父亲教授的生计毅力,挺过了父亲离家出走的损伤。
或许仅仅传德自认为挺过了。就像在小说里平平写来,电影里却拍得触目惊心的:他与父亲终究一次沿河策马,以一己之力解救他们漂往瑞典出售的木头那一段。简直赔上了十五岁的生命,传德潜入严寒激流中把堆积的木头摆开,赢得父亲的欣赏。
但拉得开的浮木和拉不开的心结恰成比照,咱们咱们都知道由于时节不对,终究只要十分之一的木材抵达瑞典。并且即便传德证明了自己渐渐的变成了一个男子汉,他的父亲也不会回来。是的,传德现已极力了,离家出走的父亲是抵达瑞典的自在河水,他却是沉留河底的木头。在河底的挣扎,仍然以噩梦出现在六十多岁晚年传德的安静隐居中,提示他那个夏天并未曩昔。
我不过出去偷个马罢了,回来就发现被偷走了终身——“外出偷马”关于传德和他的同龄老友约拿,以及他的父亲,都有不同的含义。传德是无从发泄的青春期激动,他对奔跑的愿望和对约拿母亲的愿望相同具有奥秘的梦境性。约拿在弟弟拉尔斯的悲惨剧发作之后去偷马,则是对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罪咎感的反抗
(捏碎鸟蛋则是约拿反讽天主对待生命的草率)
,但终究反抗失利,暴雨惩罚了两人。
要害是父亲是真的偷马,少年们不过是偷着骑一下。不管以“外出偷马”作为二战时父亲在挪威反抗军里的暗号,仍是作为父亲与约拿母亲的偷情隐喻,仍是他真的把地主的马偷了出来带儿子进行终究的同行,父亲都是一个赶过实际之上的浪漫主义者、冒险的急先锋。
备忘录:与自己的宽和永久不迟
终究是自在,豁出去的父亲比传德早了五十年挑选并获取了自在。对此,传德尽管受伤、惋惜,却无比神往,因而他才会在五十年后学习父亲离群索居。在这一点上,《外出偷马》成为可贵的一部不情感劫持父亲的父子情电影,有着和东方相似电影很不相同的明亮,前者里,无人有罪。就像少年传德对误杀弟弟的拉尔斯说的:这不怪你。
《外出偷马》,(挪)佩尔·帕特森著,余国芳译,北京联合出书公司2019年11月版。
晚年重遇拉尔斯,才挖出了传德内心深处真实耿耿于怀的事:他在乎的是父亲脱离他之后,是否在约拿与拉尔斯家度过了余生。他读了一辈子的狄更斯,教他自问:“假如我人生的主角不是自己?那么谁替代了我?”是拉尔斯吗?仍是约拿,乃至传德的父亲?——事实上,都不是,仅仅这种惊骇替代了被惊骇的日子自身。
相对电影的宛转,小说里更直白书写对父亲的爱情,打从父亲退伍归来便是:“……他的眼睛在搜索我,我的眼睛也在搜索他。我悄悄点个头,他也允许轻轻地一笑,一个只给我一个人的笑,一个隐秘的笑,我知道从那一刻起,就只要咱们两个人,咱们有了约好。”因而反衬出终究父亲的误期愈加残暴。两个男人的国际是自在密切的,也是对立风险的,一如漂木。
不过,在这个好像以男人为主的国际里,是几个女性充当了改变事态的要害。1999年,千禧岁除,传德的女儿忽然来访,迫使他走出一向的儿子人物——这儿电影的戏法闪现了,女儿从背影中回头,模糊间竟然是传德暗恋过的约拿母亲的样貌。就好像传德被偷走的半生不存在,短短春梦方醒罢了——直到女儿向他说出自己从小也被感染了狄更斯那种忧惧,传德刚才理解自己的虚妄。
而在五十年前,另一个不起眼的女性忽然在窘境中爆宣布强壮能量,那便是只进场过一两次的传德的母亲。金句“痛和不痛能够自己决议”,是父亲在除草时说给他听的,但证明却是由母亲的行为完结——分明失掉老公又得不到合理补偿,应失望无助的母亲,却在瑞典决议把菲薄的卖木材收入用作给儿子买了一套成人西服。仇恨与爱的转化,本来能够这么轻松,父亲未能供认的儿子的长大,母亲替他赋形。
这样一个母亲的强壮与另一个母亲——约拿的母亲相同。尽管她们本质上是所谓“情敌”,但小说与电影都没有出现这一层意思,让两人在没有交集之中逾越了尘俗的纠葛,各自从属于各自的自在。她们和传德的女儿,也因而成为在传德的三个要害时刻唤醒他的命运女神。
这下我才理解故事的当下时刻设定在千禧年前夕的含义。这是佩尔·帕特森“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告知咱们与自己的宽和永久都不或许太迟;告知咱们即便垂老仍然有重新开端的权力;咱们认为跟着一次意外而丢掉的人生,其实如影随形,谁也无法掳夺——即便是你的亲人或爱人。
作者|廖伟棠
修改|安也回来搜狐,检查更多
责任修改:

 皇派门窗荣获《2021-2022中国家居行业精品年鉴》证书
皇派门窗荣获《2021-2022中国家居行业精品年鉴》证书 星成木板静电喷粉工艺亮向家居展,是新时代年轻人首选!
星成木板静电喷粉工艺亮向家居展,是新时代年轻人首选! 吉鸿:生态家居整套一站式解决方案
吉鸿:生态家居整套一站式解决方案 容声WILL“养鲜"黑科技加持 “冰箱蔬果长7天”奥秘正式解封!
容声WILL“养鲜"黑科技加持 “冰箱蔬果长7天”奥秘正式解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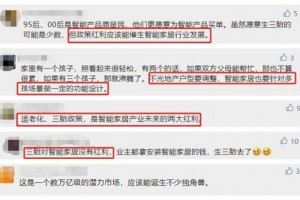 正式入法三孩政策会是智能家居的催化剂吗
正式入法三孩政策会是智能家居的催化剂吗 生活家电市场两极分化
生活家电市场两极分化 集成灶上市企业业绩增速领跑厨电华帝老板等如何搭上这班车
集成灶上市企业业绩增速领跑厨电华帝老板等如何搭上这班车 首个全国性家装质量验收标准正式发布
首个全国性家装质量验收标准正式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