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作家笔下的雪
作家笔下的雪
冰上小坦克 白雪石/绘
冰心说,“我永久喜爱下雪的天”,但是现在冬季比从前温暖多了,北方也很少下雪,即便下雪,也不能呈现“小孩站在雪里露不出头顶”(萧红)的那种大雪了。幸亏咱们还能够凭借作家的文字感触雪的魅力。
“雪不像雨,它不曾点滴凄清、愁损离人;也不曾挟风掠阵、铁马冰河;更不会敲着窗棂、打着芭蕉、拍着梧桐;而是悄悄悄悄地,在你毫不感觉中,铺满整个大地”(刘墉),雪的心爱之处在于“它的广被大地,掩盖全部,没有不同”,“朱门与蓬户相同的遭受它的沾被,雕栏玉砌与瓮牖桑枢没有不同待遇。地上上的坑穴洼溜,冰面上的枯枝断梗,路面上的残刍败屑,全都罩在天公抛下的一件鹤氅之下”(梁实秋)。
石评梅在雪夜里逛过北京城,“过顺治门桥梁时,一片白雪,模糊中望见如云如雾两行挂着雪花的枯树枝,平和坦皎白的河面”,“城墙上参差的砖缘,披罩着一层一层的白雪,昂首望:又看见城楼上点缀的雪顶,和挂悬下垂的流苏”,“过了宣武门洞,一片白地上,远远望见万盏灯火,人影活动的单牌楼,真美”,“巨大庄重的天安门,只要白,只要白,只要白,漫天漫地一片皆白”。孙福熙还见过北京的春雪,“我愿在多雪而雪不易消融的北京等候他。但是,等候着等候着,我爱的雪仍是没有来”,合理他“决计扔掉关于雪的想望,全部精力地等候春光”时,春雪却来了,“我到中华门面前,大的石狮上披着白雪,老年人怕雪而披雪兜,他却因爱雪而披上雪做的兜。他张了嘴不绝地笑,谁说只要小孩是爱雪的?”。
在老舍的眼里,济南的冬季下点小雪最妙,“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小髻儿白花,如同日本关照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当地雪厚点,有的当地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如同被风儿吹动,叫你期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比及快日落的时分,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如同遽然害了羞,轻轻露出点粉色”。
不过,在北方,要想去看真实的雪国际,只要去东北,“从冬到春,雪是永久不化的。下了一层又一层,冻了一层又一层。大地冻成琉璃板,人在上边能够滑冰”,“一片无边的是雪的国际。在山上,在原野上,在房子上,在树木上,都是盖着皑白的雪层”,“雪!皎白的雪!晶亮的雪!吱吱作响的雪!我的魂灵如同是要和它交融在一起了”。
北方下雪,不稀罕,江南的雪,却并不那么简单见到。
上海是一个几乎不下雪的城市,“可贵上个月上海下了一场雪,雪花漫天飞扬,宛如柳絮鹅毛,飘飘洒洒。极目天穹,为之心旷神怡。惋惜这美景只闪现了十分钟,大地还没有粉妆,尘土没有冰封,便仓促猝但是止”(赵清阁),“这儿毕竟是上海,似乎连一点雪的皎白也容不下,一边下,一边消融,只湿润了润滑的地上,一点痕迹也不留。倘在乡间,屋面的瓦楞该盖没了,山该白了头,树该着了花,无边的田畴也必定是耀眼的一片银装了”(柯灵)。
到过西湖的必定不少,但像钟敬文相同有幸领略过西湖雪景的却未必那么多,“飞来峰疏疏落落地着了许多雪块,冷泉亭及其他建筑物的顶面,一例地密盖着纯白色的毡毯”,“观海亭石阶上下都厚厚地堆满了水沫似的雪,亭前的树上,雪着得很重,在雪的基层并结了冰块”,“周围有几株山茶花,正在艳开着粉红色的花朵。那花朵有些落下来的,半掩在雪花里,红白相映,颜色明媚,使咱们感到华而不俗,清而不寒”。
下雪了,假如不出屋子,做点啥好呢?“窗外,冬风呼号,雪花乱飘,这时,炉火正红,壶水正沸,恰巧一位风雪故人来,一进门,打打身上的雪花,进入了我的闺阁,沏上一杯龙井,泡沫喷香,相对倾谈,放言高论。水壶咝咝作响,也恰似参加了咱们的叙谈”(臧克家),也是一件美事。在冯骥才看来,“雪夜里的灯火模糊却格外温暖。有灯火,就有人家,有炉火,有热茶,有亲情,有日子的兴趣——有了这些,就不再惧怕漫天的冰雪与人世的酷寒。此刻,人世的气味便格外诱人”。
而汪曾祺更乐意雪地利走出屋子,“到后园去折腊梅花、天竺果。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白雪,生意盎然”。
当然最期望下雪的当属孩子们,他们“毫不计较双手冻得又红又肿,只管尽心经意地堆着雪人,大大的头,长长的臂膀,也许是短短的腿。或许是握一支打狗棒,或许是手提一只旱烟袋,脸上的眉眼鼻嘴,则是用烧过的柴灰抹出来的概括,怪样子,却能引得人们看见之后哈哈地大笑一场”(李辉英)。
除了堆雪人,孩子们还能够捕鸟,“咱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位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鲁迅《故土》)。
雪总是要消融的,化得满地雪泥让人心烦,但迟子建却偏心这浑然天成的泥泞,当她走在农贸市场的土路上,“泥泞中的废纸、枯草、烂草叶、鱼的内脏等杂物若有若无,一股腐朽的气味扑鼻而来。这感觉当然比不得在永久有绿洲盘绕的西子湖畔,撑一把伞在烟雨毛毛中梦想来得惬意”,但它“依然能使我堕入另一种怀想——想起木轮车沉重地碾过它时所溅起的泥珠,想起北方的人们行进其间的困难背影,想起咱们曾有过的磨难和耻辱,我为双脚依然能触碰到它而感到欣喜”。
咱们和张炜相同,祈求着“下雪吧,下雪吧”,可雪总不来。不过,即便盼不来雪,咱们还能够“给自己的心房来一场白蝶飘动般的瑞雪”,“那些雪花可能是亲情、友谊、爱情的回味,可能是幼年往事的回忆,能够是生命进程中许多琐屑却灿烂的闪光点,能够是唯有你自知之明,或许竟含糊莫名的某些隐秘情愫”(刘心武)。
(作者:宫立,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田博群回来搜狐,检查更多
责任编辑:

 皇派门窗荣获《2021-2022中国家居行业精品年鉴》证书
皇派门窗荣获《2021-2022中国家居行业精品年鉴》证书 星成木板静电喷粉工艺亮向家居展,是新时代年轻人首选!
星成木板静电喷粉工艺亮向家居展,是新时代年轻人首选! 吉鸿:生态家居整套一站式解决方案
吉鸿:生态家居整套一站式解决方案 容声WILL“养鲜"黑科技加持 “冰箱蔬果长7天”奥秘正式解封!
容声WILL“养鲜"黑科技加持 “冰箱蔬果长7天”奥秘正式解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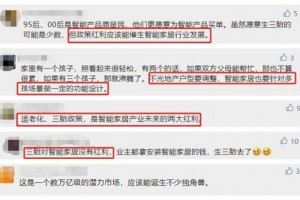 正式入法三孩政策会是智能家居的催化剂吗
正式入法三孩政策会是智能家居的催化剂吗 生活家电市场两极分化
生活家电市场两极分化 集成灶上市企业业绩增速领跑厨电华帝老板等如何搭上这班车
集成灶上市企业业绩增速领跑厨电华帝老板等如何搭上这班车 首个全国性家装质量验收标准正式发布
首个全国性家装质量验收标准正式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