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元是建筑学方面一名普普通通的学者。早在1974年以前,陈景元就完成了一部叫《骊阿集》的着作。在书中,陈景元从建筑学的专业角度阐述了阿房宫并非秦始皇所建的理论,并大胆地提出秦始皇生前并没有为自己建造过陵墓的惊人观点。
质疑一:俑坑离秦陵那么远,是秦始皇的吗?
那是 1974年11月初,陈景元到南京博物馆办事,博物馆的同志把发现兵马俑的消息告诉了陈景元。一直对秦陵抱有浓厚兴趣的陈景元特意跑到西安进行考察。陈景元是建筑学方面的一名学者,退休前在江苏省国土局工作。在兵马俑发掘现场考古队员的帐篷里,陈景元幸运地见到了当年兵马俑考古队队长、秦始皇兵马俑前任馆长袁仲一教授,然而,陈景元和袁仲一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也正是从这次会面开始的。
陈景元在这次西安考察当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疑点:从秦始皇陵到俑坑最近也要 1.5公里,如果再加上俑坑本身的宽度,这个距离还要远一些。从常理上讲,谁会把陪葬坑放在这么远的一个位置上呢?骊山是块风水宝地,除了秦陵外,周边经常会发现其他墓葬。既然这一带墓葬密度相对较大,怎么敢肯定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
他把这些疑问写出来转给考古队,希望得到信服的解释,然而没有得到回信。那么,为什么袁仲一一直没有回信呢?其实,在袁仲一看来,他和陈景元初次见面时就已经回答了陈景元的疑问。袁仲一说,秦陵范围广阔,除地宫之外,还环绕有内城和外城。兵马俑虽然在外城之外,与秦陵貌似很远,但从面积看,它们的距离是合乎比例的。对于这个解释,陈景元仍不甘心。终于,他又发现了几条有力的证据。
质疑二:秦始皇为什么放着铁兵器不用,而选择落后的青铜兵器陪葬?
在兵马俑1号和 2号坑,大量的步卒围绕着战车排成一列列整齐的大小方阵,陈景元由此推断,战车是这支部队的主力。然而,自殷周以来直至春秋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车战的弱点逐渐暴露,常常是顾得了左边顾不了右边。那么,秦始皇还会在交战时大量使用落后的战车吗?陈景元指出,秦始皇当政以后,连年的战争迫使他对军队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大量采用骑兵和步兵相配合,使之更加轻便,易于作战。从这点判断,兵马俑坑中的那支部队应该不是秦始皇的军队,它的年代肯定更早一些。
对于此,袁仲一认为,不能因为俑坑中出现战车就否定它属于秦始皇。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说秦国取缔了战车。战车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两军交战时,它在速度和冲击力上的优势是步兵和骑兵无法比拟的。兵马俑坑的军阵,正是战车、骑兵和步兵有机组合的典范。
陈景元显然并不同意这个解释,他又指出了另一个疑点:俑坑中发现了很多笨重的青铜兵器,秦始皇这样一位善于征战、统一六国的国君,会放着先进的铁兵器不用而去选择落后、笨重的青铜兵器陪葬吗?这显然有悖于常理。对于这一观点,袁仲一认为,铁兵器代替铜兵器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冶炼技术的普及需要一定时间。所以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秦代出土的兵器基本上是铜兵器,铁兵器极少,整个秦陵也只出土了两三件,以此认为铁兵器代替铜兵器与实际情况不符。
质疑三:秦始皇的强者之师,竟然连头盔都不戴?
陈景元的质疑仍没结束:秦始皇的军队既然是一支能统一六国的强者之师,在装备上也应该是一流的,然而,俑坑里的这些兵俑没有任何头盔保护。难以想象,这种简陋的武装能在近距离厮杀的战场上获取胜利。的确,在秦陵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石铠甲坑。从已经拼合起来的石盔石甲,我们似乎看到了秦国军队的威武英姿。奇怪的是,既然秦国军队配有头盔,那兵俑为什么没一个人戴呢?
袁仲一认为,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间,习性尚武,与游牧民族混居。而且,当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严苛法律:秦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或许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尚武的秦军干脆脱掉了笨重的头盔和重甲,冲上战场去杀。《史记》对秦军的这一行为也有描述:战场上的秦军竟然袒胸赤膊,索性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
质疑四:兵俑身上的奇异文字,暗示兵马俑属于秦宣太后?
1975年,《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一幅图片引起了陈景元的注意。这张图片是兵马俑的局部,上面刻有一个奇怪的文字:这个字是个月字旁加一个脾脏的脾字。虽然陈景元对秦国文字并不陌生,但这样奇异的文字还是头次见。
在秦兵马俑考古队撰写的《试掘简报》中,专家把这个字解释成“脾”字。陈景元并不认同。他翻阅了容庚编着的《金文编》和徐文镜编写的《古籀汇编》,发现构成“脾”字右半部分的“卑”字有很多形式的写法。但众多字形当中,没有一种写法符合佣坑中的那个字。就是这个字,引出了陈景元对兵马俑主人的惊人发现。
1976年,陈景元在得知西安发现兵马俑的消息后跑到了西安,在西安文管会办公室里,有关负责人小心地拿出一块秦代桶瓦给陈景元看。这块瓦上也刻着一个奇异的文字,左边的字陈景元不认识,但右边的月字还是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陈景元带着拓下来的文字回到住地南京,但之后的两年,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字,他一筹莫展。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景元在图书馆结识了南京师大古文字专家段熙仲教授。经过仔细查对,段教授认为,秦代桶瓦上左边的字为“芈”(毕)的变体字。这应该是两个独体字,读作“ 芈月”。这消除了长久以来陈景元心头的困惑,“芈”字对他来说并不陌生,秦始皇的祖母、秦惠文王的王妃——秦宣太后就姓“芈”。因此,陈景元断定,兵马俑的主人并不是秦始皇,而是他的祖母秦宣太后。袁仲一却认为,字不能这样拆,一个字拆了之后,意思就大为不同了。
质疑五:秦人尚黑,兵俑衣服为何五颜六色?
专家的解释似乎让陈景元有些失望,但他又提出了一条令人意想不到的证据——秦人以黑为贵,而兵俑的衣服却五颜六色。在发掘时,很多俑的身上还残留着一些颜料,并且从颜料的位置和颜色判断,他们的衣服是五颜六色的。在秦始皇生活的年代,金木水火土五行说十分盛行。当时周朝崇尚火德,秦始皇灭周后认为是自己的水攻克了周的火,因此把水德作为崇拜对象。而在秦代,五行里水相对应的颜色就是黑色。秦始皇还把“尚黑”作为一项法令颁布。既然如此,俑坑中出土的这些衣着五颜六色的兵俑如果放在秦始皇时代就很难解释得通,但如果放在宣太后的时代,就会得到合理解释。
袁仲一却认为,秦代尚黑,只能说明秦人以黑为贵,要求在重大场合中着黑衣,并不是要求全国人民不能穿其他颜色的衣服。陈景元觉得袁仲一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那么,面对陈景元一次又一次的质疑,袁仲一在想什么?
质疑六:陪葬的戈,为什么会在淤泥层发现?
袁仲一说,1号坑出土了很多秦代兵器,其中在一种被称做“戈”的兵器表面,明确刻有“五年相邦吕不韦戈”的铭文。
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兵器生产。而陈景元指出,在俑坑的考古报告中一共就提到过5个有“相邦吕不韦”字样的戈,其他兵器都没有明确的年代标志。比如,俑坑中还出土了一些被称做“铍”的秦代兵器,这些兵器上只注明了“十七年”“十八年”,仅凭这很难判断它们属于哪个历史时期。吕不韦在任不过10年,在秦始皇12年时就死了。所以,标有“十六年”的铜铍肯定不是指“吕不韦十六年”,由此推断,除了5个刻有“相邦吕不韦”铭文的戈外,其他没明确纪年的兵器应该都不是秦始皇时代所造。
袁仲一则指出,在很多兵器上都能看到刻有“寺工”字样的铭文。寺工是秦始皇设立的专门负责制造兵器和车马器的国家机构,这明确说明兵马俑是秦始皇时期所建,主人是秦始皇。陈景元拿出一张照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张照片泄露了“吕不韦戈”出土时的一个小秘密——它不是在俑坑的地砖上出土,而是在离地砖有一定距离的淤泥层上被发现的。如果“ 戈”和俑坑处于一个年代,为什么它没出现在俑坑的地砖上,而是跑到距离地砖29厘米到250厘米的淤泥层上了呢?
对此,兵马俑研究专家说,铜戈最初是由兵俑拿着,处在一个悬空的位置。近2000年来,俑坑可能因为地面渗水和洪水等自然原因涌入大量的水流而形成淤泥层。有一天,悬空的铜戈因为失去载体,掉到了淤泥层上。专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近乎完美的解释,有关谁是兵马俑主人的讨论似乎也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虽然,兵马俑坑的考古工作至今还没结束,但相信,随着秦始皇陵周边的考古勘探工作不断推进,考古专家的深入研究,笼罩在秦始皇陵上面的迷雾将逐渐淡去,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将是一段真实的秦国历史,一个恢宏的地下王国。

 皇派门窗荣获《2021-2022中国家居行业精品年鉴》证书
皇派门窗荣获《2021-2022中国家居行业精品年鉴》证书 星成木板静电喷粉工艺亮向家居展,是新时代年轻人首选!
星成木板静电喷粉工艺亮向家居展,是新时代年轻人首选! 吉鸿:生态家居整套一站式解决方案
吉鸿:生态家居整套一站式解决方案 容声WILL“养鲜"黑科技加持 “冰箱蔬果长7天”奥秘正式解封!
容声WILL“养鲜"黑科技加持 “冰箱蔬果长7天”奥秘正式解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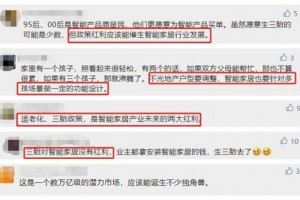 正式入法三孩政策会是智能家居的催化剂吗
正式入法三孩政策会是智能家居的催化剂吗 生活家电市场两极分化
生活家电市场两极分化 集成灶上市企业业绩增速领跑厨电华帝老板等如何搭上这班车
集成灶上市企业业绩增速领跑厨电华帝老板等如何搭上这班车 首个全国性家装质量验收标准正式发布
首个全国性家装质量验收标准正式发布